爱情是一种病。来时如山倒,走时如抽丝。
——题记
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自己,二十天,二十天似是而非的发生在一辈子的经历中是不是可以完全忽略。
一个刚刚开始就已经终结了的故事。一个刚刚谋面就开始告别的人。
这一切,是不是可以忽略。欢笑,以及痛苦。
北方的冬季异常萧索,荒凉。
周末。黄昏。我穿上银色的羽绒服,戴一顶银色的手编六角帽,去一个邻近的城市见他。
这是我第三次,也是今生最后一次见他。
他不知道这将是最后的诀别。我没有告诉他。我甚至不想再和他说任何一句话。不是气愤,不是怨恨。是因为一切言语都不再有意义。当我们再次彼此面对的时候,已经成为两个完全无关的个体。
我只想取回我应该取回的东西。带回家,放到一个永远不再触及的地方,或者彻底焚毁。
一切都不该有痕迹。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发生又不断遗失的过程。所以我从来不给告别过的人任何消息。象高中毕业时,同学们互赠照片,彼此在留言本上写珍重和祝福的话。我没有。亦从不对任何人表达。因为讨厌以物质的方式承载内心最柔美的情怀。
一些事情,看似有始有终。只是多么完整的经历回想起来都是零星的碎片。所有曾经深深触动过灵魂的细节,最终都会在时光的沙漏中泻失,消亡。
这次也一样。我知道。
在多彩网吧门前,他低着头瑟缩地站在寒风里。看过去依旧那么瘦,鼻子上依旧架着那副诙谐的黑框眼镜。
我在他面前停下来。两只脚规矩地并拢在一起,下额埋进衣领,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。没有说话。我不想说话。因为不知道能说什么。
你来了。他说。
书。我侧扬起脸,神色黯然地看着他。眼睛里透露出一股桀骜不逊的冷漠与倔强。
他从怀里掏出我想要回的东西。我接过来,转身离开。
你去哪?
我没有回答。一边走一边掏出火机,把这本自己曾经最爱的书点燃。我知道,我其实不是在烧这本书,而是在烧自己的心。用不了多久,它就会和这书一样变成灰烬,连同我和他之间似是而非的爱情。
我以为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,但是我没有。我的脚步如此坚定,尽管没有方向,却不再感觉茫然。这一刻终于明白,原来疼痛的尽头是平静。万念俱灰的心就象一座沉睡的大山,再也听不到虫鸟的啁啾。
你干什么?
他看到我出乎意料的举动,气愤地追上来,紧紧抓住我的胳膊,夺去已烧毁一大半的书。
放开我。
我没有看他,压低声音,从牙缝里冷冷地逼出这几个字。
你不是已经同意我们做最好的朋友了吗?……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原谅我!对不对?
他用力摇着我的肩膀,几乎失去理智地向我吼着。我依旧没有看他,使劲挣脱他的双手飞快跑到马路对面,拦住一辆出租车,头也没回地走掉了。
一直觉得,也许这个故事就该以这样的场景作为结局。
至于他在马路对面以什么样的神情面对等待散场的观众……。一切都已经与我无关。愤怒,沮丧,无奈,亦或难过。一切,一切。
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前不久出现在梦里那只亲吻我后背的蓝色蝴蝶。为什么它要一直跟在我身后,为什么在它变成王子时我会从梦中醒来。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一种暗示。我不明白,却总觉得这个梦与我和他之间的故事有关。
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穿着一件蓝色毛衣,在一家网络公司看招聘广告。当我的目光触到那件毛衣的一瞬间,内心忽然掠过一种恍如隔世的惊觉。仿佛我是一个历尽沧桑的浪人,在世间流落亿万斯年,只为等待前世里注定的一段尘缘。
虽然那一刻我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我正在找的男人,但直觉告诉我不会错。因为那毛衣的花纹与颜色和梦里蝴蝶的翅膀竟如此相似。
一边想着,我一边快步朝他走去。在与他水平相隔半米远的地方停下来,两只脚规矩地并拢在一起。低着头,掏出手机在写短信一栏里打下三个字:我来了。发送。几秒钟后,我听见诺基亚短信提示声从他的身上传来。
骆可。我没有抬头,轻声唤他的名字。
他转过头,凝视我良久,然后走过来牵起我的手向科技城门口走去。一路上,我们在人群里穿梭,他没有说一句话。神情忧郁。
若干年后,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记得他手掌心的温度,但那一刻却清晰地感觉到内心同时暗涌着的希望与绝望。仿佛红、蓝两种颜色的血液在交织,奔涌。一种带来温暖,一种带来冰凉。
梦里的那只蝴蝶,在它变成王子时,我并未来得及看清王子的容颜。所以,一切都将是幻影,我知道。这个故事刚刚开始,就已经有了浓郁的结局的味道。不是圆满,而是破碎。
骆可和我都是将要被生活溺死的人。去看他,希望彼此安慰和鼓励,如此而已,可见面后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在这个陌生的城市,他背井离乡,一个人漂泊多年。曾经深深爱过一个大他七岁的离婚女子,以及她的孩子。最终却因为她的背叛而放弃,从此失掉爱的勇气和能力。
忘掉她。忘掉她就不会再有痛苦。
和他并排坐在洁白的床单上,我尽量找着安慰他的语言,可这句毫无意义的话刚一出口就感到它的苍白无力。如果一切真的可以那么轻易地忘记。如果……如果能够成立吗?都是同样茫然无助的人,谁又能将谁救赎。笑。
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事情,现在回想起来如同一场梦境。梦醒了,一切都不复存在。唯独留存下来的记忆是他在后背上的一记吻。如那只蓝色蝴蝶一样,轻轻的。一个瞬间温暖一生,瞬间亦成为永恒。也就是在这个瞬间,我听见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:离开这个男人。
离开。
既然无法彼此救赎。
第二次见到他已是初冬。两个人依旧沉默地沿街而走,细小的雪花在不定向的冷风里打转,乱舞,落在脸上后迅速被皮肤的温度融化。脸颊变得冰凉。喜欢这种冰冷,可以让内心坚定。
有人说,如果在初冬的第一场雪那天,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,就会和他坠入爱河。笑。知道这都是受过伤的人编出来自我安慰的谎言。虽然虚空,却在某段困惑的时间里,带给人暧昧、朦胧的期盼。
姗,我已变坏,无法再做回自己。你是个好人,我不想伤害你。我们做好朋友吧。最
好的最好的那种,行吗?
那天,在静静的莱茵河咖啡语茶,骆可终于对我讲了那女人走后他堕落的生活,他的数不清的女人。
我也和她们一样,对吗?为什么要骗我?
强忍着内心的疼痛,我一字一句地问他。
不,你不属于她们之中任何一个类型。相信我。你是一个好人。对你,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玩弄和欺骗。曾经真的希望和你认真地交往、相爱,过回正常人的生活,只是后来发现从这片沼泽里拨出已经太难。
把头别向窗外,我看着眼前似在一瞬间开始坍塌的冷森建筑。骆可的声音被内心翻滚着的疼痛的潮涌淹没,渐渐虚无。
挪开他压在我手上的手,我从包里掏出烟来点着。因为不想自己流泪,任何时候,任何人面前。
离开,最后一次告诉自己。
如果不能相爱,那就迅速伤害。
那段遗忘的时间里,经常在周末,一个人乘车去很远很远的野外,赤手举着相机随意拍照。雪地里斑驳的足迹,枯死的树,幽深寂寞的老井。
天气如此寒冷,手指冻得无法伸直。一个人没有目的的四处游窜。只想寻回那种丢失已久的纯粹、快慰的感觉,是除了自然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感觉。
苍茫的灰色天空下,常有鸽子盘旋而过。
许多年来,一直喜欢冬天,因为它最接近生命的本色。可以治疗灵魂受到的伤害,让烦躁的心安宁。
就象那一片片飞雪。洁白的,纯粹的。倾天而来,覆盖了所有裸露在大地上的物体,浮光掠影一样的斑驳往事也被深深掩埋。世界变成一幅轻描淡写的水墨画。所有曾经疼痛难忍的伤口渐渐在这幅简约的画中褪去颜色,一点点变得模糊。
生命恢复简单。时光在平静中默默流去。带走稍纵即释的年华。
骆可,这个冬天里结识的男人。20天的琐碎情节,若有若无。不是游戏,不是欺骗,只是与爱情无关。如一片从天上飘下来的雪,悄无声息地落在茫茫原野上,闭起眼睛沉沉睡去。等待着春天某个温暖的时刻,苏醒融化,消失不见。
说过的,已不记得。未说完的,不想再知道。
彼岸天堂的河岸有蝴蝶在飞翔。摆渡的人已失去踪影。
你又何必为难自己?
——题记
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自己,二十天,二十天似是而非的发生在一辈子的经历中是不是可以完全忽略。
一个刚刚开始就已经终结了的故事。一个刚刚谋面就开始告别的人。
这一切,是不是可以忽略。欢笑,以及痛苦。
北方的冬季异常萧索,荒凉。
周末。黄昏。我穿上银色的羽绒服,戴一顶银色的手编六角帽,去一个邻近的城市见他。
这是我第三次,也是今生最后一次见他。
他不知道这将是最后的诀别。我没有告诉他。我甚至不想再和他说任何一句话。不是气愤,不是怨恨。是因为一切言语都不再有意义。当我们再次彼此面对的时候,已经成为两个完全无关的个体。
我只想取回我应该取回的东西。带回家,放到一个永远不再触及的地方,或者彻底焚毁。
一切都不该有痕迹。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发生又不断遗失的过程。所以我从来不给告别过的人任何消息。象高中毕业时,同学们互赠照片,彼此在留言本上写珍重和祝福的话。我没有。亦从不对任何人表达。因为讨厌以物质的方式承载内心最柔美的情怀。
一些事情,看似有始有终。只是多么完整的经历回想起来都是零星的碎片。所有曾经深深触动过灵魂的细节,最终都会在时光的沙漏中泻失,消亡。
这次也一样。我知道。
在多彩网吧门前,他低着头瑟缩地站在寒风里。看过去依旧那么瘦,鼻子上依旧架着那副诙谐的黑框眼镜。
我在他面前停下来。两只脚规矩地并拢在一起,下额埋进衣领,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。没有说话。我不想说话。因为不知道能说什么。
你来了。他说。
书。我侧扬起脸,神色黯然地看着他。眼睛里透露出一股桀骜不逊的冷漠与倔强。
他从怀里掏出我想要回的东西。我接过来,转身离开。
你去哪?
我没有回答。一边走一边掏出火机,把这本自己曾经最爱的书点燃。我知道,我其实不是在烧这本书,而是在烧自己的心。用不了多久,它就会和这书一样变成灰烬,连同我和他之间似是而非的爱情。
我以为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,但是我没有。我的脚步如此坚定,尽管没有方向,却不再感觉茫然。这一刻终于明白,原来疼痛的尽头是平静。万念俱灰的心就象一座沉睡的大山,再也听不到虫鸟的啁啾。
你干什么?
他看到我出乎意料的举动,气愤地追上来,紧紧抓住我的胳膊,夺去已烧毁一大半的书。
放开我。
我没有看他,压低声音,从牙缝里冷冷地逼出这几个字。
你不是已经同意我们做最好的朋友了吗?……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原谅我!对不对?
他用力摇着我的肩膀,几乎失去理智地向我吼着。我依旧没有看他,使劲挣脱他的双手飞快跑到马路对面,拦住一辆出租车,头也没回地走掉了。
一直觉得,也许这个故事就该以这样的场景作为结局。
至于他在马路对面以什么样的神情面对等待散场的观众……。一切都已经与我无关。愤怒,沮丧,无奈,亦或难过。一切,一切。
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前不久出现在梦里那只亲吻我后背的蓝色蝴蝶。为什么它要一直跟在我身后,为什么在它变成王子时我会从梦中醒来。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一种暗示。我不明白,却总觉得这个梦与我和他之间的故事有关。
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穿着一件蓝色毛衣,在一家网络公司看招聘广告。当我的目光触到那件毛衣的一瞬间,内心忽然掠过一种恍如隔世的惊觉。仿佛我是一个历尽沧桑的浪人,在世间流落亿万斯年,只为等待前世里注定的一段尘缘。
虽然那一刻我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我正在找的男人,但直觉告诉我不会错。因为那毛衣的花纹与颜色和梦里蝴蝶的翅膀竟如此相似。
一边想着,我一边快步朝他走去。在与他水平相隔半米远的地方停下来,两只脚规矩地并拢在一起。低着头,掏出手机在写短信一栏里打下三个字:我来了。发送。几秒钟后,我听见诺基亚短信提示声从他的身上传来。
骆可。我没有抬头,轻声唤他的名字。
他转过头,凝视我良久,然后走过来牵起我的手向科技城门口走去。一路上,我们在人群里穿梭,他没有说一句话。神情忧郁。
若干年后,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记得他手掌心的温度,但那一刻却清晰地感觉到内心同时暗涌着的希望与绝望。仿佛红、蓝两种颜色的血液在交织,奔涌。一种带来温暖,一种带来冰凉。
梦里的那只蝴蝶,在它变成王子时,我并未来得及看清王子的容颜。所以,一切都将是幻影,我知道。这个故事刚刚开始,就已经有了浓郁的结局的味道。不是圆满,而是破碎。
骆可和我都是将要被生活溺死的人。去看他,希望彼此安慰和鼓励,如此而已,可见面后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在这个陌生的城市,他背井离乡,一个人漂泊多年。曾经深深爱过一个大他七岁的离婚女子,以及她的孩子。最终却因为她的背叛而放弃,从此失掉爱的勇气和能力。
忘掉她。忘掉她就不会再有痛苦。
和他并排坐在洁白的床单上,我尽量找着安慰他的语言,可这句毫无意义的话刚一出口就感到它的苍白无力。如果一切真的可以那么轻易地忘记。如果……如果能够成立吗?都是同样茫然无助的人,谁又能将谁救赎。笑。
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事情,现在回想起来如同一场梦境。梦醒了,一切都不复存在。唯独留存下来的记忆是他在后背上的一记吻。如那只蓝色蝴蝶一样,轻轻的。一个瞬间温暖一生,瞬间亦成为永恒。也就是在这个瞬间,我听见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:离开这个男人。
离开。
既然无法彼此救赎。
第二次见到他已是初冬。两个人依旧沉默地沿街而走,细小的雪花在不定向的冷风里打转,乱舞,落在脸上后迅速被皮肤的温度融化。脸颊变得冰凉。喜欢这种冰冷,可以让内心坚定。
有人说,如果在初冬的第一场雪那天,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,就会和他坠入爱河。笑。知道这都是受过伤的人编出来自我安慰的谎言。虽然虚空,却在某段困惑的时间里,带给人暧昧、朦胧的期盼。
姗,我已变坏,无法再做回自己。你是个好人,我不想伤害你。我们做好朋友吧。最
好的最好的那种,行吗?
那天,在静静的莱茵河咖啡语茶,骆可终于对我讲了那女人走后他堕落的生活,他的数不清的女人。
我也和她们一样,对吗?为什么要骗我?
强忍着内心的疼痛,我一字一句地问他。
不,你不属于她们之中任何一个类型。相信我。你是一个好人。对你,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玩弄和欺骗。曾经真的希望和你认真地交往、相爱,过回正常人的生活,只是后来发现从这片沼泽里拨出已经太难。
把头别向窗外,我看着眼前似在一瞬间开始坍塌的冷森建筑。骆可的声音被内心翻滚着的疼痛的潮涌淹没,渐渐虚无。
挪开他压在我手上的手,我从包里掏出烟来点着。因为不想自己流泪,任何时候,任何人面前。
离开,最后一次告诉自己。
如果不能相爱,那就迅速伤害。
那段遗忘的时间里,经常在周末,一个人乘车去很远很远的野外,赤手举着相机随意拍照。雪地里斑驳的足迹,枯死的树,幽深寂寞的老井。
天气如此寒冷,手指冻得无法伸直。一个人没有目的的四处游窜。只想寻回那种丢失已久的纯粹、快慰的感觉,是除了自然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感觉。
苍茫的灰色天空下,常有鸽子盘旋而过。
许多年来,一直喜欢冬天,因为它最接近生命的本色。可以治疗灵魂受到的伤害,让烦躁的心安宁。
就象那一片片飞雪。洁白的,纯粹的。倾天而来,覆盖了所有裸露在大地上的物体,浮光掠影一样的斑驳往事也被深深掩埋。世界变成一幅轻描淡写的水墨画。所有曾经疼痛难忍的伤口渐渐在这幅简约的画中褪去颜色,一点点变得模糊。
生命恢复简单。时光在平静中默默流去。带走稍纵即释的年华。
骆可,这个冬天里结识的男人。20天的琐碎情节,若有若无。不是游戏,不是欺骗,只是与爱情无关。如一片从天上飘下来的雪,悄无声息地落在茫茫原野上,闭起眼睛沉沉睡去。等待着春天某个温暖的时刻,苏醒融化,消失不见。
说过的,已不记得。未说完的,不想再知道。
彼岸天堂的河岸有蝴蝶在飞翔。摆渡的人已失去踪影。
你又何必为难自己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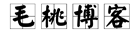 毛桃博客
毛桃博客







评论前必须登录!
注册